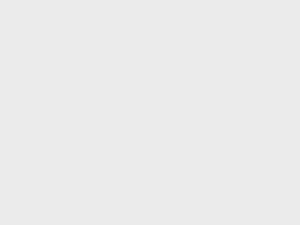风暴眼|阿富汗ICU住进中国商人:陪护穿防弹衣擦AK,10块雇一个保镖
2021年08月25日 10:30:51来源:风暴眼
喀布尔陷落之前,我被确诊了新冠。
文/Vicky
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如果在机票软件上查询未来半个月“伊朗-广州”的航班,软件会跳出冷冰冰的一行字——
“您好,近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家航司都相应调减了国际客运航班数量。您查询的德黑兰(THR)至北京(BJS)的机票可能因无航班或航班座位已售完导致暂时无法查询到对应价格。”
贴心的软件给了另一个选择,若是选择公务机包机,回国的时间可定制,每架飞机可搭载15人。只是人均价格高达64473元。
对于滞留伊朗的刘峻铭来说,价格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他本该在8月23日和同事一同登上回广州的班机,8月24已经回国开始隔离,但曾在阿富汗确诊新冠的经历改变了这一切。
他并不知道这次的源头是什么、还是之前简陋的医疗环境让他还未治愈,刘峻铭只知道,他又感染了。
和在阿富汗确诊不同,他不必担心塔利班随时攻占医院、各方势力可能冲进医院绑架中国人,也听不见窗外时有时无的枪声和炮声,但再次确诊,意味着回国时间无限期延后。
目前,伊朗赴华的旅客,若是曾确诊过新冠疫情,需要向使馆申请健康码,而健康码的获得,需要接连进行肺部检查(肺部CT或X光结果正常)、采样间隔不短于24小时的核酸检测、登机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和IgM、IgG检测。
若任何一个流程复阳,回国之旅立刻中断。
算上8月24日,刘峻铭已经在迪拜、阿富汗、伊朗停留了44天。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我们和刘先生聊了聊他的故事。
一、在赫拉特感染
7月11号,我先飞了迪拜。在迪拜大概停留了两天,我就飞了阿富汗。
(广州飞迪拜机上合影)
我的公司是电池制造配套商,主要给电池生产企业提供成套生产设备,并且提供后续服务。这次去阿富汗是出差,我们在阿富汗有一个工厂,相当于我们出机械,给这些国家输出中国制造。
阿富汗这个国家是非常落后的,他们的平均工资,月薪差不多200~400人民币吧,因为有战争,明天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当地人基本拿日薪,每天差不多10块钱人民币。人力非常便宜,但是阿富汗人干活特别勤快,拼命的干活,只要给钱。
我刚去赫拉特(阿富汗第三大城市)没多久,差不多10来天吧,事情还没做完,我就发现我感染了。
7月27号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说这时候感冒,我太难了。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得了新冠。因为新冠的症状和普通感冒还是有点差别的。
(刘先生微博)
一开始是发烧,偶尔会有高烧,低烧基本没断过。并且会口渴、有鼻涕、有痰,咳嗽咳出来会有血。普通感冒怎么会咳血呢?然后因为发烧,我身上的肌肉也会发酸、发痛。
我感觉不妙之后,就去问了我上海医科大的朋友,跟他讲了一下我的症状,他跟我说,新冠总共有十几条症状,你这对上了八九条,你逃不掉了,赶紧走吧。
可是那个时候我走不了,只能困在赫拉特。
(刘先生公司在赫拉特的工厂)
本来我们工厂离机场很近,大概就2、3公里吧,当时觉得自己病了嘛,打算第二天飞喀布尔的,结果就在飞的前一天晚上,机场被塔利班占领了,我没飞出去。
并且因为赫拉特一直在战乱,医院什么的都封锁了,我也不敢去医院。加上医院全部都是感染者,去医院也不安全,我就没去医院,就在住的地方硬扛,扛了七天。
赫拉特的晚上基本天天都可以看到战斗机、直升机啊飞来飞去的,塔利班就开枪打他们,可以看到子弹飞过去飞过来的光线,当时其实也不怎么害怕,习惯了。一开始合作伙伴怕我们担心,说是政府军演练,但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7月29号凌晨的时候,空袭开始了。我当时听到一整片的轰炸声响彻天际,之后就是进攻,机枪扫射不断,冲突大约持续了2个多小时吧,最近的子弹还打穿了我们的窗户。
后来,大使馆还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刘总你怎么还不走,想点办法赶紧定航班,国家外交部都打电话来了,叫你赶紧撤回国。我就和大使馆的人说,现在没有航班,大使馆就跟我重复强调说,赶紧走,赶紧想办法定航班,赫拉特这里塔利班都已经打到你公司周边了,还有三、四公里。
那我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定航班,去喀布尔,当时是第二天的航班。然后我们听说,我们那航班被塔利班控制了。
所以没办法,我就继续在赫拉特住的地方硬扛,也没有人照顾,不需要人照顾,就自己吃吃药什么的。刚开始的时候早中晚都在发烧,早上一般是38度9、39度这样,然后到了中午会好一些,变成37度8、37度9、38度左右。
期间有一次,合作伙伴喊我去他们家吃饭,当时因为塔利班已经开始打了,合作伙伴就说来吃个饭,家宴。我跟他说,我在发烧,我感染了(新冠),你家里有孩子,不然还是算了吧。
我们合作伙伴完全不在意,他说没事的没事的,我们这种伊斯兰教的人,我们有神明保佑,不会感染的,你看,我们都很健康。我就在他家吃了饭,他家6个孩子,我那天晚上发烧烧到了40度,直接给我烧睡着了。
而且合作伙伴离我们工厂差不多3、40分钟车程,晚上在打仗,我们一行7、8个人,加上翻译就在他家睡了一晚上。因为阿富汗政府是有飞机的,但是塔利班没有飞机,所以塔利班就晚上打仗、攻城,因为政府军如果想用飞机轰炸,晚上看不见,不知道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不敢乱轰炸。
后来也没听说这家人有没有感染,应该是没什么事。但是他们挺有代表性的,阿富汗人普遍不怎么把新冠当回事,或者说大点,他们都不怎么把生死当回事的,因为劳动力便宜,再加上常年打仗,擦枪走火受伤都很正常,感觉人没有什么价值。
我个人觉得,他们这种态度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吧,可能让我没有那么害怕了。
刚开始我去阿富汗的时候,我是要求我们工厂里的工人都戴口罩的,那些工人有伊朗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大家都在一起干活,他们都不喜欢戴口罩,我们当时还从国内带了一千只口罩过来,一一发给他们,要求他们每天必须戴。一开始没人听,戴着戴着就不戴了,后来我就设立了一个奖惩方式,不戴口罩的人罚款1美金,慢慢的他们才开始戴。
(工厂工人正在调试设备)
并且,赫拉特这个城市是没有核酸检测做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不管感染没感染,阿富汗本地人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扛扛可能就过去了,扛不过去就死了。他们也不在意。
我是没办法,并且我也不想在那种情况下去医院,又是交叉感染又是塔利班的,所以我就在住的地方呆了7天。
感觉当时也快要待到极限了,有一天特别临时,说下午2点的航班,早上10点通知我要我们走,当时跟我们说,赶紧走,安检也不用安检,直接给送进机场了,就随便搜了搜身上有没有带武器啊什么东西,我们就上飞机了,当时也快没位置了。
二、在喀布尔住ICU
我离开赫拉特的三天后,塔利班占领了赫拉特。
但是当时我也顾不上这些了,我到喀布尔的第二天,就感觉自己要扛不住了,平时呼吸都要呼吸不上来了。8月2号的时候,我住进了ICU,做肺部检查的时候发现肺部已经感染了50%~60%。
能想象吗,我千里迢迢从中国来阿富汗,在赫拉特硬扛了七天,机场还被塔利班占领,搞了多少方法才从赫拉特来首都喀布尔,结果喀布尔的ICU还有蚊子还有苍蝇!进出ICU的医生别说防护服了,连口罩都不戴!
结果院长和我说,这已经是我们这里条件最好的病房了。医生也过来和我说,你的病就是这个样子了,该吃的药,该打得特效药我都给你打了,你要生要死,就要靠基督教和佛祖保佑了。我当时问那个医生,他在湘雅医院学习过,会一点简单的中文。我问他,我说你的医术不是很高超吗?学术水平不也很高吗?那个年轻的医生跟我说,“NO!NO!我高超的医术就是看着说明书给你打针!”
我当时真的欲哭无泪。我在又有蚊子又有苍蝇的ICU住了七天,花钱请了两个陪护,早晚轮班端着把AK,有点保镖性质的那种陪护。陪护天天给我吃什么?吃烧饼!烤肉!烤羊腿!
为什么呢?因为阿富汗没有白米饭。他们也没有喝粥的习惯,我生着病,肺部感染了50%,就想喝口粥,吃点清淡的养养胃。结果陪护觉得我付了钱,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天天给我烤羊腿,油炸的羊腿、烤串、烧饼。
我连吃了七天。
陪护天天拿着一杆AK在擦,走来走去,他们也穿着防弹衣。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老板离不开呼吸机,除了吃饭摘下来,别的时候天天在床上躺着,万一枪响了,老板也没有防弹衣,你们保镖拿着个AK,到时候全跑了。
中间我还打了两针特效药,美国研制的药,从迪拜空运过来的。总共是运了三针过来,但是打了两针我就不敢打了,药效太给劲了。特效药打下去三分钟,我就开始发抖,我就跟医生说天哪我快死了,不要打了。然后主治医生走了,另一个医生来了,他又给我打了一针,我问他你打的什么?医生说特效药,然后我立刻又开始发抖,就那种一秒钟感觉可以抖一千下的感觉,好像牙没动,但是床在狂抖。
抖完之后,我直接就秒睡了,感觉像跑了1千公里。
不过特效药打完之后,整体症状就好多了。我没事儿就开始斗地主。有一天我拿着手机在ICU病房里斗地主,手机上联网的欢乐斗地主,然后阿富汗的医生来检查,说“哇塞,刘,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太厉害了!我觉得你是中国人里最帅的!我给你跳个舞吧!你好好玩!”所以我的病房一直是整个医院最热闹的,他们喜欢来我这里开会。没事儿就问我,“刘,你的症状怎么样了?”
在ICU的时候,晚上觉也睡不好。旁边的保镖端着把AK,动不动就“咔”一声上膛,玩他那个枪,我就有一搭没一搭的睡。一般我晚上8、9点钟就躺下开始睡,睡到11、12点起来,看下书、玩下手机,然后到1点再睡,3点又起来。就这么断断续续的睡觉。加上身体也不舒服,老要咳嗽,别人睡觉可能是一件美滋滋的事,我睡觉是痛苦的事儿。
在ICU住了7天,我出院了。出来直接瘦了10斤。
当时听说有其他帮派要绑架中国人,我心想,我钱还没有花完,这医院就一个保镖,还天天在那玩枪,说不清楚是我保护他还是他保护我呢,天哪太不安全了,还不赶紧跑,所以大约10号的时候,我就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账单,大概花了8000美金吧。7天,8000美金,ICU病房里还有苍蝇有蚊子。
要说后不后悔走这一遭,我觉得也是没办法。我们开始的计划是两个月从广州到曼谷、然后到迪拜、从迪拜到阿富汗,阿富汗调试一个多月,再去伊朗从伊朗转机回广州。
结果没想到,阿富汗突然就乱了,我看新闻美国说塔利班今年可能都占领不了阿富汗,我们才决定去的,因为觉得政府的判断还是可以相信的,结果没想到全世界都错估了塔利班的速度,我也比较戏剧化,又是新冠、又是战争、还担心会不会被帮派绑架。
后来阿富汗大使馆给我们打电话,说让在8月10号全部撤离,我们就想了各种办法,在8月12号的时候离开了阿富汗。
大使馆真的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阿富汗的时候,大使馆差不多2小时就会打一次电话过来,询问是否安全、核酸怎么样、血清怎么样。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阿富汗和伊朗的大使馆多次沟通,为我们特别开通了绿色通道,也使得我们离开阿富汗的效率大大提高。据我所知,外交部还为了在阿的中国人,向当时的阿富汗总统和政府官员特别提出,要保证所有在阿中国人的安全。
包括我的家乡厦门市政府、外事局、商务局,也时时刻刻担心着我的近况,关心我们团队的处境,一直在跟进我的情况以便提供帮助。不得不说,只有置身海外,并且面临战乱、疫情,各种各样戏剧化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祖国对自己国民的关怀。加上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情况,我常常感叹,祖国强大还是好。
三、两车保镖
因为感染,我一直都在医院和住处呆着,以前的时候我每天可以走两万步,一年差不多能走四千公里,结果在阿富汗的时候我每天就只走100步。现在在伊朗也是。
从房间出门,上电梯,电梯上7楼,吃早餐,下电梯,回房间。
我一般都会等别人吃完,或者别人还没去的时候去,最早或者最晚的时候去,每天三餐都在同一个地方。快郁闷死了。感觉可能感染新冠没死,郁闷郁闷死了。
在阿富汗的时候,我住的地方一进门,就没信号了,可能有时候有人敲敲门,一开门,发现是塔利班。进门就没信号,没办法,只能出门。后来我发现,在门口能有两格信号,我每天就守在门口、坐在地板上靠着门,看看有没有信号、有没有流量,天天都在守门。
局势不稳,加上身体状况不好,如果没有吃的了什么的就会让当地人去买。非常痛苦,阿富汗不能喝酒,也没有中餐,只能自己做。最糟糕的是,这个地方连鸡蛋都是假的,人工鸡蛋。
如果非要上街呢,我得带两车人上街。两车保镖。就跟黑社会一样,前面一辆皮卡、后面一辆皮卡,我们坐中间那辆车。
保镖都是阿富汗人,有现役的和退役的,现役的话一天10美元的样子,但他们是按年的。阿富汗这种国家就是,给钱就行,给钱就能享受总统出行、黑社会老大出行的待遇。
四、惊险机场 离开阿富汗
12号的时候,我们离开了阿富汗。
当天上飞机也是,心惊肉跳。
这个国家整个已经比较混乱了,而且他们落后,不像国内,可能安检、各个政府机构都联网,他们不是,他们全靠人工。
12号我是早上10点的航班,飞伊朗。我住的酒店离机场就10分钟,我6点半就出发了,6点40就到了机场,然后开始东跑西跑办各种手续,还有安检。他们安检不像咱们国内,过机器就行了,他们都是手工安检,大包小包,一个个打开看,然后反复摸你身体,上下摸,看有没有带枪、武器之类的,完了还要脱鞋、脱袜子。
而且,因为我的签证当时过期了两天,所以我还去一个部门补办了一下签证,交了罚款。
正常来说,交完罚款就通过了,手续完成了,可以上飞机了。结果到了机场,我拿着罚完款的证明、机票、各种手续的证明单子,坐航班,结果被告知不能过去,因为这个部门他们不认我交的这个罚款。因为这些单据什么的都是手写的,然后盖个章,机场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收到通知。
最后我连飞机票都被收走了,闹也没用。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喀布尔他们这个机场不是自己管的,是土耳其管的,我就托了各种关系、各种人,找到机场的老大,直接花钱,连机票都不用,直接塞钱把我塞上了飞机。塞了大概500美金。
我6点40到机场,10点的航班,我上飞机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座位了。不算给机场负责人塞的这500美金,之前花钱买票都花了差不多5000人民币,我怎么也得上去。
最后还是依靠了中国人的智慧,成功上了那趟飞机,到了伊朗。
我离开喀布尔三天后,塔利班进城,宣布占领喀布尔。
(在喀布尔做核酸检测)
我觉得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每次离开阿富汗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三天后就被塔利班占领,但是说运气不错,我们一同出差的5个人,几个员工都没事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天天调侃我,就我一个人感染了。连我们的合作伙伴也会调侃我,“刘,所有人想感染都感染不了,你老玩手机,所以你感染了!"
8月23号的时候,我的团队们都坐上飞机离开伊朗了。
但是我因为确诊,只能继续留下。
现在每天喊医生来酒店打点滴,来一次大概给100美金,医生都开心的不得了。但是我不开心,症状比之前好很多,现在是心率加快、呼吸不畅。伊朗这边也是不打疫苗、不戴口罩,每天能增长几万例,我觉得医院也不太安全,就还是在酒店呆着。
结语:
凤凰网财经联系刘先生的时候,他正筹划23号离开伊朗归国的事宜。直到8月22日,刘先生再次联系记者,说好想回国,但是他二次感染了,只能在酒店目送团队登机。
虽然为团队高兴,但交谈中刘先生还是流露出一丝怅惘,“过两天我得再去办签证,办逗留签,因为按规定我只能在伊朗待21天,现在已经10天了,也不知道还要再呆多久。”